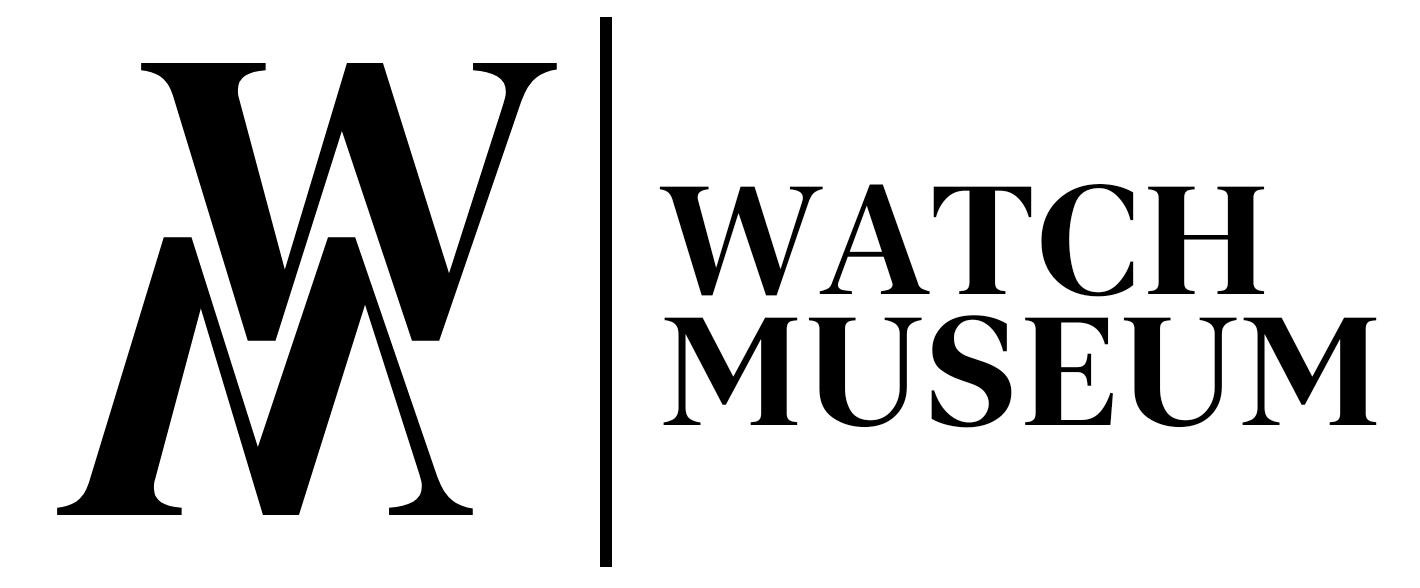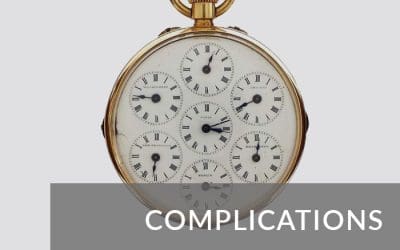縱觀歷史,計時的方法和重要性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反映了人類社會不斷變化的需求和技術進步。 在最早的農業文化中,時間的劃分就像白天和黑夜一樣簡單,由陽光的存在決定。 這種基本的方法已經足夠了,直到公元前 1500 年左右日晷的發明,它使得希臘和羅馬等古代文明能夠將一天「劃分」成更易於管理的時間間隔,稱為「小時」。 然而,日晷對陽光的依賴導致其局限性,促進了更複雜的設備的發展,例如公元前1000 年左右的水鐘。 。 公元 8 世紀沙漏的引入提供了更可靠的替代方案,儘管它對於長期計時來說仍然不理想。 直到 1300 年代,歐洲僧侶出於對精確祈禱時間表的需求,才發明了第一批機械鐘。 這些由重量驅動並由擒縱機構調節的早期時鐘具有開創性,但仍然缺乏廣泛使用所需的精度和便攜性。 伽利略·伽利雷於 1583 年發現的擺原理標誌著精度的重大飛躍,使時鐘能夠以每天秒為單位測量時間。 然而,直到發條機構的出現,便攜性的挑戰仍然沒有得到解決,這最終導致了懷錶的誕生。 這項創新標誌著真正便攜式計時的開始,徹底改變了人們與時間互動和理解時間的方式。
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精確計時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除了幾千年前沒有任何方法可以保持準確的時間之外,根本沒有必要這樣做。 早期以農業為基礎的文化,只要太陽照耀就開始運轉,天黑後就停止運轉。 直到人類開始擺脫純粹的農業社會,人們才開始尋找一種更精確地標記時間流逝的方法,而不是簡單地將每一天劃分為「白天」和「夜晚」。
已知最早的將一天分解為更小的時間塊的裝置是日晷,它至少在公元前1500 年就被發明了。的人的名字將永遠消失在歷史中意識到你可以將一根棍子直立在地上,透過標記陰影落在哪裡,將日光分成離散的時間間隔。 這些間隔最終被稱為“小時”,每個小時是每天太陽照射時間的 1/12。 日晷是個絕妙的主意,它使古希臘和羅馬文明得以有序發展。 日晷的一大優點是它非常便於攜帶。 然而,它確實有一些非常基本的缺陷。 首先,它只有在陽光明媚的時候才有效。 這在晚上不是問題,因為無論如何沒有人在黑暗中工作。 但這在陰天時是一個大問題。 然而,即使在陽光明媚的情況下,一年中白天的長度也會發生變化,這意味著從夏至到冬至,「一小時」的長度也會有多達 30 分鐘的變化。
由於日晷的局限性,人們尋找其他不依賴太陽的方法來測量時間的流逝。 非常受歡迎的早期嘗試之一是水鐘 [也稱為漏壺],於公元前 1000 年左右發明。透過特殊標記的容器底部的孔洞漏出,可以標記時間的流逝。 水鐘比日晷準確得多,因為流速不受一天或一年中時間的影響,而且無論陽光是否照耀都沒有關係。 不過,它們也並非沒有嚴重缺陷。
雖然水可能看起來以穩定、固定的速度滴落,但事實上,容器中的水越多,由於水的重量施加的壓力,漏出的速度就越快。 古埃及人透過使用側面傾斜的容器來平衡水量減少時的水壓來解決這個問題。 然而,其他問題包括這樣的事實:隨著時間的推移,滴水的孔往往會變得更大,從而允許更多的水更快地通過,而且逃生孔也有被堵塞的嚴重趨勢。 但願天不會冷到讓水真正結冰的程度! 就其本質而言,水鐘也不是特別便於攜帶。
好吧,沒多久,人們就意識到水並不是唯一穩定流動的東西,接下來是沙漏,它是在公元 8 世紀左右發明的,它沒有更早發明的主要原因可能只是因為在此之前沒有人能夠夠好地吹製玻璃。 沙漏使用沙子從一個玻璃容器通過連接兩個玻璃容器的微小開口流入另一個玻璃容器,並且沙子的通道不會特別受到導致水鐘和日晷出現問題的事物的影響。 然而,大沙漏是不切實際的,長時間計時通常意味著在一天中一遍又一遍地轉動沙漏。 基本上,它是一個很棒的計時器,但卻是一個糟糕的計時器。
直到 1300 年代,情況一直如此,當時歐洲的一群僧侶決定他們確實需要一種更好的方法來判斷何時該祈禱。 因為,你看,僧侶的生活圍繞著固定的祈禱時間表進行——黎明時一次,日出時一次,上午一次,中午一次,下午一次,日落時一次,夜幕降臨時一次。 因此,知道正確的時間不僅是一件好事,更是一種宗教要求! 結果,這些僧侶設計出了第一批已知的機械鐘。 順便說一下,“時鐘”這個詞來自荷蘭語中的“鐘”,因為這些早期的機械鐘沒有指針,只是為了報時而設計的。
除了報時裝置之外,這些早期的時鐘還有兩個重要的要求。 第一個是動力源,由附在繩子或鏈條上的重物提供。 重量被運送或拉到時鐘的頂部,重力將完成剩下的工作。 第二個是透過某種方式迫使重物以緩慢、有節奏的速度下落,而不是像鉛重物一樣直線下降。 這是由一個美妙的和
一項巧妙的發明稱為擒縱機構。 簡而言之,擒縱機構是一種定期中斷重物下落路徑的裝置,使其一次一點點而不是一次全部下落。 這其實就是時鐘「滴答作響」的原因,因為當擒縱機構前後移動,交替嚙合和釋放連接到擺錘的齒輪時,它會發出非常獨特的聲音。
這些最早的時鐘雖然是科技奇蹟,但並不是特別準確。 此外,雖然他們允許將小時細分為更多的分鐘部分[因此我們用“分鐘”這個詞來表示小時的第一個小部分],但他們無法將小時細分為進一步的或“第二個」小部分[並且是的,這也是這個字的由來]。 這要等到1583 年左右,一位名叫伽利略·伽利萊(Galileo Galilei) 的相當聰明的年輕人發現了鐘擺的原理。總是需要相同的時間來擺動回來,並且向前。 事實上,他發現鐘擺返回所需的時間是由鐘擺本身的長度決定的,而不是由擺動的寬度決定的。 而且,透過將精確測量的擺錘安裝到時鐘的擒縱機構上,鐘錶匠能夠生產出每天精確到秒而不是分鐘的鐘錶。 對鐘擺施加多大的力並不重要,因為該力只影響擺動的寬度,而不影響鐘擺本身的長度。
因此,現在我們擁有的時計無論在一天中的哪個時間或哪個季節都可以正常工作,並且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非常準確。 不幸的是,它們仍然不是特別便攜,因為重量不會定期下落,並且如果受到外部運動,擺錘就無法正常工作。 這就是懷錶發揮作用的地方。
讓時鐘變得可攜帶的關鍵發明是彈簧。 事實上,遊絲的使用可能是繼擒縱機構發明之後第二重要的鐘錶發展。 製造便攜式時鐘的第一步是用無論時鐘放置在什麼位置都能施加穩定力的東西來取代用於為其提供動力的重物。 人們發現,緊密盤繞的高張力金屬條在展開時會或多或少地施加穩定的力,這使得它非常適合這項工作。 當然,沒多久,鐘錶匠就注意到發條在鬆開時所施加的力越來越小,但他們想出了一些相當巧妙的方法。
處理該問題的方法,包括“stackfreed”和“fusee”等設備。
使時鐘真正便攜的第二步是提出鐘擺的替代品,使時鐘以精確的時間間隔滴答作響。 早期的「便攜式時鐘」使用一種稱為「foliot」的裝置,該裝置由懸掛在旋轉平衡桿兩端的兩個非常小的重物組成,但這些裝置既不是特別準確,也不是真正的便攜式。 然而,新發現的彈簧概念再次拯救了我們。 人們確定,可以將非常細的線圈(由於太薄而稱為“遊絲”)直接連接到擺輪上,並且當來自主發條的力傳遞到擒縱機構時,連接的遊絲將盤繞並以非常規律的速度展開,從而使擒縱機構以所需的精確定時間隔嚙合和釋放。 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無論時鐘如何握持,這都是事實,從而提供了真正的便攜性。
這些第一批早期便攜式時鐘和第一批真正的懷錶之間的區別是模糊的。 雖然彈簧驅動的時鐘可能早在 1400 年代就已經開發出來,但彈簧調節的時鐘直到 1600 年代中期才出現,不久之後它們就變得小到可以隨身攜帶在腰間或放在口袋裡。 很快,任何買得起懷錶的人都攜帶著一項風靡一時的新奇發明——懷錶。